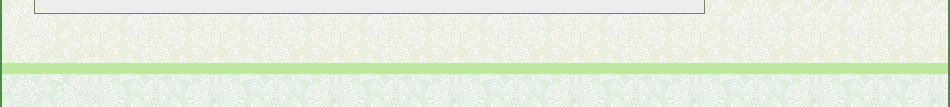挑着行李上科大
阮耀钟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门(北京)
1958年我浙江金华一中高中毕业,那年我很走运。第一个走运的是我被免试保送。也就是说,我不必“一颗红心,二种准备”了,也不必参加竞争激烈的高考了。我看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招生广告,特别喜欢,可惜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浙江不招生。当时让我们填三个保送志愿,三个保送志愿我填的是:清华大学电机系,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,最后一个是浙江大学电机系。为什么我把清华大学电机系填作第一志愿呢?说来好笑。在我老家诸暨,把青蛙又叫做田鸡,“清华电机”与“青蛙田鸡”谐音,人们常说“青蛙田鸡”,“ 青蛙田鸡”,我想清华大学电机系一定很有名,于是就把它填作第一志愿了。
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很晚才收到,收到一看,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,是我最喜欢的学校,最希望进的大学,我真高兴,我真走运,这是我的第二个走运。并且我录取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技术物理系,又是我最喜欢的专业。我在念小学时,曾问过老师一个问题:“天有多高?天有没有顶?天若有顶,那顶上面一直一直一直上去又是什么?”当时老师的回答不能使我满意,我对自然界充满好奇,对科学充满向往。
我高中物理老师毛颖可的物理课讲得特好,高中三年我一直是物理课代表,即使高三担任学习委员了,仍兼任物理课代表。我的物理成绩一直是班上最好的,在考试前,我还给班上同学们讲过物理辅导课。我高中毕业能进自己最喜欢的大学和最喜欢的专业,并且这所大学本来在浙江不招生,我的运气真是太好了!
1958年9月初我从老家浙江诸暨农村,挑了一担行李来北京,一头是一只向亲戚借来的旧板箱,另一头是铺盖卷。因为以前我去金华念高中时,每次来回都乘的是每个小站都停的慢车,所以我去北京乘的自然也是慢车。在诸暨到上海的车上,有位好心人跟我讲,到上海火车站加个快,可直达北京,免得一次次转车。可是,我到上海火车站一看,从上海加快到北京,要四块多人民币,舍不得这四块多,还是继续乘慢车吧。一路停了多少个站也记不清了,坐了几天几夜,才到北京。最狼狈的是在南京,那个年头还没有南京长江大桥,南京站下车后,要自已赶到轮渡码头,怕赶不上轮渡,挑着行李几乎是小跑,一跑,箱子把手跑断了。这只旧箱子还是我妈妈向亲戚借来的。当时真把我急坏了,幸亏身上带了根备用绳子,匆匆忙忙、手忙脚乱地系上了,继续跑。
一路上转了多少次车也记不得了,最后一次转车是天津。在天津站换车时我碰到了第一个科大同学──朱惜辰,他后来跟我是一个班。他跟我说过二句话,至今我还清楚记得。这二句话都是他父亲跟他讲的,他父亲是个高级知识分子。第一句话是看数学之类的书时,旁边一定要放一张纸,一枝笔,因为中间推导步骤书上往往是忽略的,要自已去推一遍。这其实就是华罗庚说的念书第一步,要先“从薄到厚”,然后再“从厚到薄”。第二句话是,一进了考场,要有自信,即使被某道题目难住了,也不要慌,这道题我做不出来,别人也做不出来,先继续往下做。分专业后,我与朱惜辰不是一个专业,大学毕业后我们一直没见过面,遗憾。
在北京前门火车站我碰到的科大同学当然多了,但我不记得碰到了那些同学。陈兆甲一直记得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第一次碰到我时的印象:剃个光头,穿了双草鞋(其实是布鞋,这是他们记错了,也许是因为我“土”的印象对他太深了),挑了一担行李,操一口浙江土话……,活像现在刚进城的打工仔。我与陈兆甲不是一个班,但分专业后都是低温物理专业的,并且陈兆甲、曹烈兆和我,科大毕业后一起留校,我们三个老同学一起共事几十年,彼此从未红过脸,难得。遗憾的是2014年曹烈兆同学先我们走了,就剩陈兆甲和我了,我们二个是联系最密切的大学同学,亲如兄弟。
在北京前门火车站看到有科大的校车来接新生,使我这个乡巴佬感到意外。
到科大报到时,问我从那里来的,我想当然是浙江啰,但是在浙江省的名单中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,最后在二机部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,原来是二机部从浙江招了批学生,我是二机部送到科大代培的,是曲线进科大。
为了从何而来,把我折腾了半天。我记得幸菊芳同学为了找他的宿舍也折腾了好半天。我们报到前,学校已把我们的宿舍事先分好了,可是幸菊芳同学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宿舍,后来发现原来是搞错了,按照他的名字,把他分到女生宿舍去了。现在幸菊芳同学已把他的名字改为幸勇,我猜想也许是为了避免再次出现类似麻烦。
(2008年2月10日 原载我的新浪博客,此博客是2007年9月6日创建的,但是2017年2月16日被封)
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_4e5f987f01008bve.html